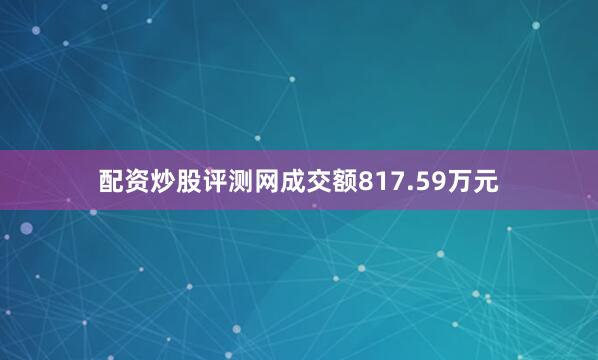威尼斯有史以来第一个VR影厅,2016年|©️Tati
那一年是2016年,威尼斯的空气像往常一样潮湿而浓烈,红毯上的镁光灯和水城的暮色交叠在一起,仿佛为影史再一次写下某种暗示性的开篇。对于大多数观众而言,那一届电影节并无特别不同:明星依旧,评审团依旧,水上交通依旧缓慢而拥挤。但在丽都岛的某个角落,一个不大的放映空间被临时搭建起来,没有银幕,没有环绕音响,白色的椅子上只放着一副 VR 眼镜,镜框里嵌着三星手机,椅背上挂着索尼耳机。我带着半分怀疑半分好奇的神色,坐下,戴上,世界便安静了。眼前浮现提示:“wifi 已连接”,随即第一部360度VR故事长片《耶稣 VR——基督的故事》开始了。
与其说那是一次观影,不如说是一种介入:每个人在各自孤独的黑暗里,被送往另一种“幕布”之内。坐在旋转椅上的观众不得不不断扭头、仰望或低头,去捕捉四周正在发生的细节。画质粗糙,表演仓促,但当火把从身边经过,当星空在头顶亮起,甚至当自己化身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时,那种古怪而又震撼的体验让我意识到:这是一次彻底不同的观影逻辑。不过很少有人在当时意识到,这个小小的VR剧场,会在几年后成为威尼斯最具实验性和前沿性的版块,也成为世界电影节制度对“沉浸式艺术”最重要的一次接纳。

拉扎雷托韦基奥岛(Lazzaretto Vecchio)
威尼斯总喜欢制造这种历史节点。1932年它率先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电影节,为电影作为艺术建立了舞台。八十多年后,它又率先为虚拟现实腾出空间。2017年正是VR电影的转折点,威尼斯电影节设立了名为“Venice Virtual Reality”的正式竞赛单元,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在A级电影节中得到制度认可的VR单元。它没有被安排在某个边角,而是获得了完整的奖项体系、专门的展映空间和一个几乎神秘的地理舞台:拉扎雷托韦基奥岛(Lazzaretto Vecchio),一个需要乘船才能抵达的隔离岛。观众购票、登船、登陆,在孤立的岛屿上排队、换上头显,再进入一个与现实不再相连的时空。威尼斯赋予VR的,不只是一个展示机会,而是一种仪式感。它仿佛在提醒人们:电影节不仅仅是胶片与银幕的庆典,它还可以是媒介未来的实验场。
初始的几年,人们依然带着“新奇”的眼光看待VR。那些作品多半是三百六十度的影像,观众仿佛被安置在球体的中央,四面八方都充满了画面。头部的转动成为镜头的替代,空间音效则制造一种临在感。可是,这种观看也迅速暴露了局限:没有剪辑,没有景别变化,故事只能以一种笨拙的方式推进。于是,真正的革新来自那些敢于把“互动”引入叙事的人。2017年,劳瑞·安德森与黄心健的《沙中房间》(La Camera Insabbiata)让观众在一片粉笔绘制的黑色虚空中自由飞翔,文字像尘土一样飘散,记忆与诗歌在空气中回荡。它获得了那一年的最佳VR体验奖。这不仅仅是对技术的颂扬,更是对叙事边界的拓展:观众第一次意识到,自己不再是被动的看客,而是故事发生的必要组成部分。

Bloodless (2017)
另一部获奖作品《血尽无痕》(Bloodless)则走向相反的方向。韩国导演金绮泳用360°的纪实影像还原一名被驻韩美军杀害的女性性工作者最后的行程。观众被放置在她的脚步里,陪伴她穿越寒冷的夜色。没有互动,没有游戏机制,只有直视与见证。这部作品证明,即便在技术狂热的氛围里,VR依然可以保有电影的伦理重量。威尼斯在同一年同时奖励了《阿登的觉醒》(Arden’s Wake)《沙中房间》和《血尽无痕》,这三条路线——动画诗学、互动飞行、纪实证言——构成了之后所有VR作品的基本坐标。
2018年与2019年的威尼斯VR更像是一次语法的打磨。人们逐渐学会了如何使用六自由度(6DoF, Six degrees of freedom)的交互,把观众的身体动作转化为叙事的动词。《人生轨道》(A Linha)用微缩舞台与手势操作讲述两个木偶人物的爱情犹疑,观众的推动或迟疑成为故事的一部分。它像是一部可以反复演奏的乐曲,每一次的触碰都会微妙地改变节奏。另一部《钥匙》(The Key,2019)则让观众在一连串任务与象征之间体验难民的旅程,直到最后交出一把象征性的“钥匙”。这是政治现实在虚拟空间中的诗意转写。与此同时,《消失的奇伯克女孩》(Daughters of Chibok,2019)用360°影像还原尼日利亚被绑架女孩的母亲们的证言,把VR变成一种“空间见证”的媒介。威尼斯的奖项结构在这几年逐渐稳定下来:最佳沉浸作品、最佳互动体验、最佳线性叙事。它像一张地图,鼓励创作者在不同方向上继续探索。

Daughters of Chibok(2019)
真正的转折来自2020年。疫情让一切物理空间戛然而止,威尼斯的红毯依旧,但观众无法成群结队登陆沉浸岛。于是,VR单元成为唯一一个可以完全转入线上并依然存活的部分。它更名为“Venice VR Expanded”,在VRChat和Viveport等平台上搭建起虚拟展馆。世界各地的观众,只要拥有一台头显,就能以虚拟化身进入这个数字岛屿。有人在虚拟咖啡厅偶遇,互相挥手致意;有人在展厅之间穿行,像逛艺术博物馆一样进入不同作品的入口。这种体验在某种意义上比线下更具共同体感:地理被抹平,大家都以数字身体在同一个空间里存在。评审团依然颁出大奖,《家中的刽子手》(The Hangman at Home)在虚拟舞台上探讨“旁观”与“责任”,而《寻找潘多拉》(Finding Pandora X)把希腊神话改造为一场多人互动的戏剧。威尼斯在疫情的阴影里意外完成了一次大胆的试验:影展不再是一个物理地点,而是一种跨地域的世界建造。
2021年延续了这一模式,《歌利亚:玩转现实》(GOLIATH: Playing with Reality)获得大奖,它通过游戏与精神疾病的交织,讲述现实与幻觉的摇摆。另一部《巴黎舞会》(Le Bal de Paris de Blanca Li)则是一次华丽的舞会,观众戴上头显,成为舞伴,与虚拟的角色共舞。这些作品让人意识到,VR已经超越了“观看”的边界,它更接近表演艺术、互动剧场、心理体验。威尼斯的勇气在于,它没有要求这些作品必须与电影相似,而是承认它们以新的方式继承了电影节的精神:用影像与叙事探索人的经验。

The Man Who Couldn’t Leave (2022)
2022年,单元正式更名为“Venice Immersive”。名字的变化是一次声明:沉浸艺术的范围已经远远超过虚拟现实的窄义。它包括混合现实、现场表演、空间装置与虚拟世界。那一年,陈芯仪的《无法离开的人》(The Man Who Couldn’t Leave)以360°影像重现白色恐怖的监狱生活,观众被迫在幽暗的牢房里与受难者共处,体验历史的阴影。它证明,即便在最传统的三自由度(3DoF)形式里,VR依然可以产生震撼的政治与情感力量。另一部《广场物语》(From the Main Square)则把观众置于一个逐渐极化的社会空间,看着秩序一步步走向崩塌。这些作品的共同点在于,它们不仅展示了空间,更展示了空间中的历史与权力关系。威尼斯给了它们最高奖项,仿佛在宣告:VR不只是奇观,而是“经验的政治学”。
到2023年与2024年,威尼斯沉浸单元已经成为创作者与观众每年必赴的聚会。《给路人的歌》(Songs for a Passerby,2023)让观众以第一人称走在街道上,听见内心的声音,仿佛在自己与世界之间开启一场对话;《线迷宫》(Ito Meikyū)则以抽象的线条与音律构建迷宫,让观众在感官的涡旋中迷失又重生。这些作品的共同点是,它们已经完全摆脱了“技术演示”的色彩,而进入一种成熟的艺术语言。观众开始期待的不再是“VR能做什么”,而是“VR能说什么”。威尼斯,作为电影节的制度化平台,为这种转变提供了保障。

Face Jumping (2025)
回顾这段历程,会发现VR在威尼斯的成长是一部双重叙事:一方面是技术的演进,从3DoF到6DoF,从单机到网络,从VR到XR;另一方面是制度的演进,从边缘试水到正式竞赛,再到线上化、再到全面更名。威尼斯的价值恰恰在于,它用电影节的权威和节奏,把这种新媒介安置在一个稳定的语境里。它告诉世界:沉浸艺术不是孤立的炫技,而是可以像电影一样被评审、被讨论、被观众共同经历。
也许我们可以说,威尼斯为虚拟现实撑起了一块第二重幕布。第一重幕布是银幕,它把世界切割成二维的影像;第二重幕布是头显,它把观众包裹进三维的空间。前者让人们凝视,后者让人们在场。两者并不冲突,它们共同扩展了“电影”的边界。正如1932年的威尼斯证明电影值得一个节日,2017年的威尼斯也证明VR值得一个节日。今天,当我们在沉浸岛或虚拟世界里排队、戴上头显、进入一个陌生的故事,我们也许正在延续电影百年来的那种最基本的渴望:在黑暗里寻找另一个世界的光。

原名朱旭斌,深度影迷分子,旅居丹麦,于2010年创办了迷影网(Cinephilia.net)。
No Newer Articles
财富牛-安全炒股配资门户-配资平台排行榜第一名-短线配资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